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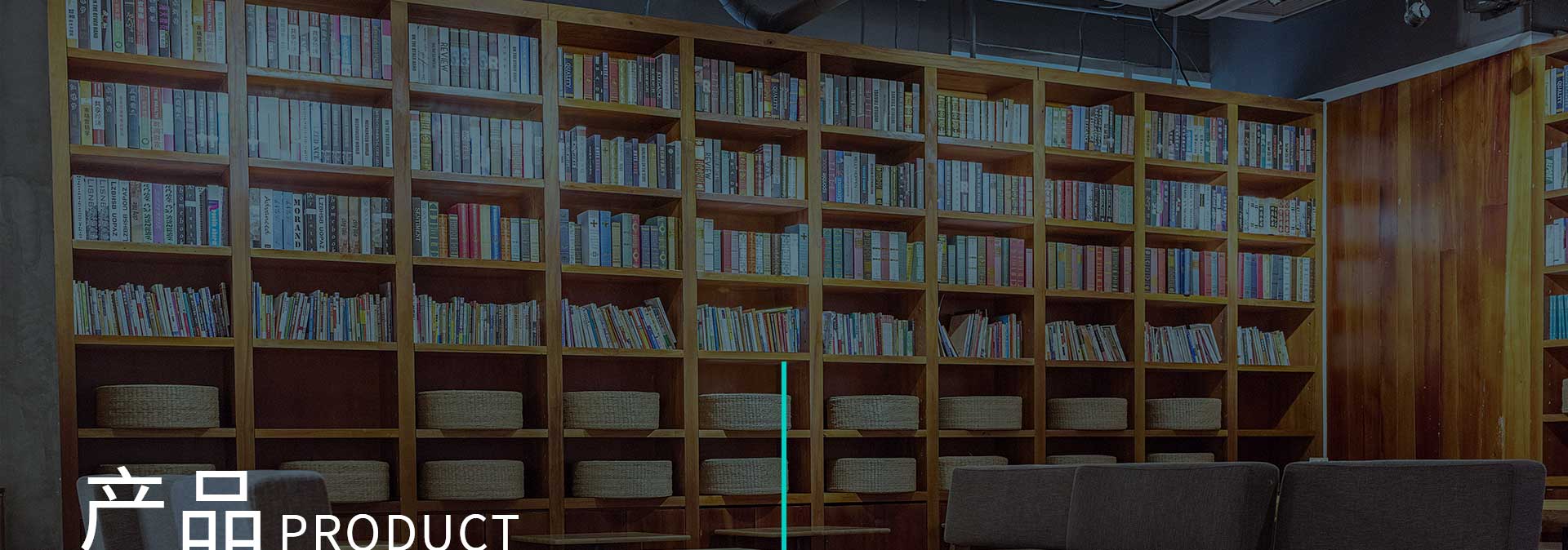

什么是老年?“我”如何面对“我”的老去?
什么是老年?多老才算老?这是我们讨论老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如何界定老年与一个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有直接的关系,也与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生活的环境有紧密的关联。如果以一个国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标准,那么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甚至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预期寿命都会有所不同。例如,不同地区的人类预期寿命有显著区别,日本、中国香港和冰岛地区的平均寿命超过80岁,但塞拉利昂、赞比亚、斯威士兰等赤道以南国家的人均寿命在今天仍旧只有40岁。生活在战火纷飞、资源匮乏的年代与生活在安稳和平、衣食充足的年代,人们的预期寿命也会有很大区别。此外,社会福利政策和医疗保健服务的水平也会影响人口的平均寿命。一个社会向老年人提供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服务,老年人在社会中能够获得怎样的生活安排,交通和通信系统对老年人的可及性,社会允许或期望老年人进行哪些工作,以及年轻人如何在公共场所或私人场所对待老年人,都可能影响这个社会中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所以,“老年”有其社会性的维度。不是说对一个人的饮食营养、运动锻炼等习惯做出明智的选择就可以轻易改变或推迟衰老。虽然个人选择会对某些衰老方式产生影响,但大部分衰老过程由遗传因素、社会状况和塑造日常生活的公共政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中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取决于社会力量,取决于这些社会力量能否向其公民提供健康的食物、可能的工作机会、足够的医疗服务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老龄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受环境、资源和社会关系深刻影响的过程。一个人能否活到老年,发挥何种功能,享有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是由其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社会角色、社会支持的深度和广度所决定的。
年龄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
“国际上对老年人的年龄划分主要基于退休年龄的界定,而在中国传统的家庭领域,‘老’主要根据家庭角色来界定。”以退休年龄来界定老年人是工业社会的发明,它将一个人是否具备社会所需的生产力作为界定“老”的分界线,“老年人”是那些不再进入社会生产,以领取退休金来维持生活的人群。这种界定相对消极,它参照的是个体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位置。它将工作置于一个人生活的中心,因此退休也时常涉及生活安排的改变。与之相对,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眼中的老年人是那些辛苦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在家,帮助子女照顾孙辈,颐养天年的至亲。这种定义老年的方法参照的是一个人在家庭和代际传递中的地位,家庭关系在此占据了重要的比重,因此这种对“老”的界定相对比较积极。樊浩教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老龄”话语中有两条线,即自然线和伦理线。“龄”是生命的自然线,古人由齿识龄,以牙齿作为人和动物的年轮或于世界中在场时间的标识,谓之“年龄”。而“老”是生命的伦理线,在中国话语中,“老”具有丰满甚至神圣的伦理意义,“老师”之“老”体现的是一种伦理上的身份认同,饱含伦理的情怀、诉求和坚守,是一种伦理上的尊敬、肯定。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作为传统、知识和历史的维护者,具有特殊的作用。他们往往维持着一家之长的地位和权威,“老”意味着享有特权和威望,它的正面含义较多。但随着现代社会尤其是信息社会的到来,老年人不再独有对知识和智慧的掌握,他们的地位动摇了,社会的崇老文化开始瓦解。许多老年人由于跟不上信息社会的技术要求,成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出行、看病都受到影响。此外,由于老年人口被视为被抚养人口,增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以及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在人口统计学中老年人口被描绘为一个社会的重负。“老”的意义变得负面了。
人口老龄化有着深刻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根源。当一个社会的出生率急剧降低,并伴随着老年人死亡率降低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老了,这就是所谓的老龄化。可见,“老龄社会”是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降低导致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一个社会中能够从事生产的人口比重下降,需要社会抚养的人口比重升高,就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一定挑战。此外,消费主义所鼓吹的青春文化,致使在公共领域中可见的都是年轻的身影,衰老的躯体越来越不可见。“衰老”不仅成为“活力”的对立面,也成为“丑陋”的同义词。苏珊·桑塔格在《衰老的双重标准》中曾谈到,随着工业化的世俗社会的到来,青春成了幸福的隐喻。青春的代名词是速度、美丽和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定义成就、名望和成功的特征。与之相对,衰老的人体就像一台坏掉的机器或一款过时的软件。在一些崇尚功利主义的西方社会,年龄变成了道德理论中的一个歧视性因素。老年人进入道德争论的方式是由于他们成了社会和经济的负担,引发了人们对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或医疗资源的讨论,这种看法使我们讨论规范意义上好的老龄化(good aging)变得愈发困难。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要求一直将尊老敬老视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这让我们从正面思考老年问题有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依托。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衰老”(aging)“老年”(oldage)并不是同义词。“衰老”是人一生中持续进行的一个过程,在生物学上指的是与时间相关的生理过程的恶化,而“老年”是按时间顺序来计算年龄的一个结果,它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一个特定阶段。“老年”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概念,而是一个充满文化意涵的社会表达,是个体生命历程中必经的特殊阶段。波伏瓦曾指出,“老年”的内涵并不确定。它一方面被看作是一种生物现象,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具有某种特殊性,但它也会引发心理上的后果,有些行为被看作是老年人特有的。“老年”更是一种存在的感受,因为它改变了人与时间的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人与世界,与其个人历史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老年阶段与其他年龄阶段一样,是社会分层与标记的需要,老年人的身份是社会强加给他的。老年学科涉及的一个主要悖论是,所有人都会变老,但在人们生命的某一个特定阶段他们被标记为“老年人”,在此之后他们的生命被看作是衰退的,需要医学干预。这正是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在现代社会产生的一个简单背景。
如果“老年”被等同于退化与疾病,那么随之而来的关于衰老的研究就是医学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尽管老年医学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患有慢性病、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不稳定和失智的老人,但医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专科,即“抗衰老”或“再生医学”,其重点不在于疾病的治疗,而在于恢复某些传统的体征。它关注的是抗老化,包括更换或再生人类细胞、组织或器官,以恢复或建立正常功能。这与社会崇尚青春文化密不可分。总体来讲,医学对“老年”的界定基本是负面的。
与老年医学聚焦于老去的身体不同,老年社会学要解决的是身体之外的衰老问题。它不再询问“人为何要衰老”,而是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后果。例如,国家或政府应如何管理老年人口?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会对经济整体产生何种影响?如何提升生育率以降低人口结构中的老龄比例?因此,确定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构成成为一国政府的工作重点。这些问题关注的是关于生命过程的社会分层,而不是它的生物学性质。老年医学和老年社会学聚焦于老年群体,其目标在于解决这一群体的健康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与之相对,老年哲学与老年伦理学考察的是老年这一生命阶段对于人的整体生命而言具有何种存在价值和伦理意义,它们不仅将“老年”放入人的生命过程中加以考察,也关注作为个体的老年人将如何面对老年的挑战,活出老年的意义。
——节选自《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