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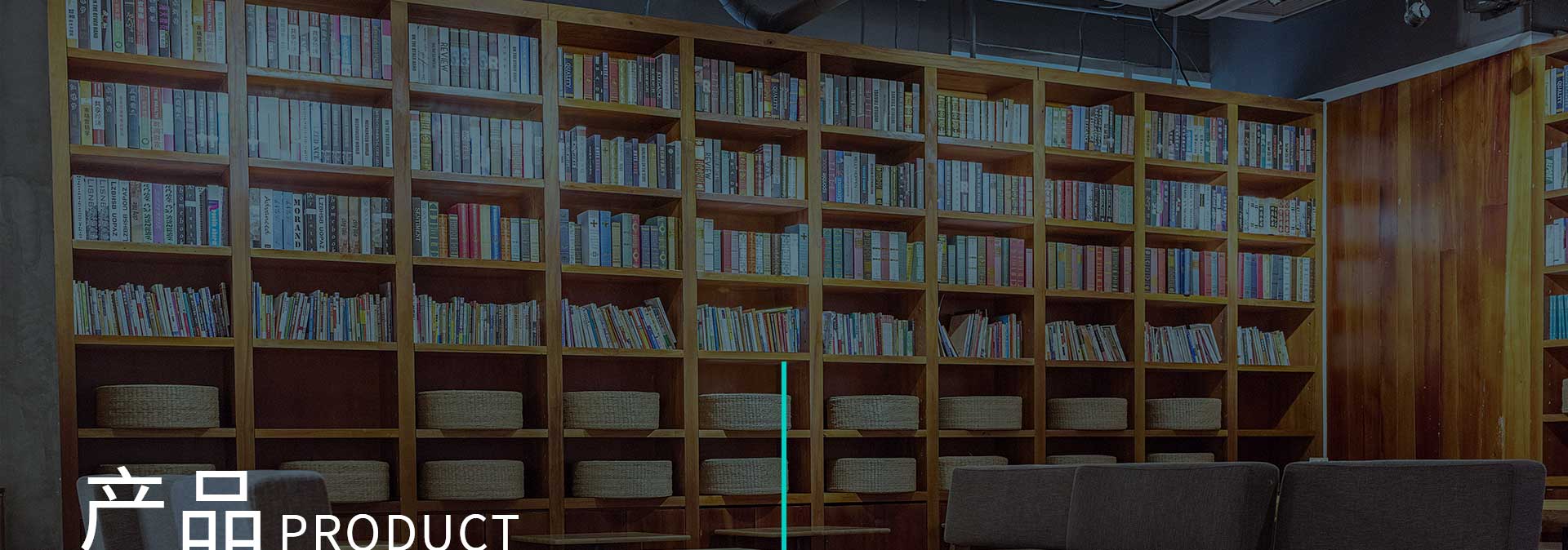

《拉康派论情感》| 克莱特·索莱尔倾力之作,有力回击了“拉康派不谈情感”的批判

在《拉康派论情感》这本书中,作者沿袭了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对结构概念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像语言一样结构化”的可解析的无意识开始,延续到无意识—啦啦语、实在的无意识、不可解析的无意识。书中行文思维缜密,逻辑清晰。
书中,作者重点探讨了拉康思想中经常被误解的不重视情感这一问题,肯定了拉康认为经验中确实存在着无法进入语言的东西等观点。书中还追踪了拉康有关情感产生的理论以及一系列特定情感理论的发展,讨论了情感在实践方面的影响等问题。
书中,克莱特·索莱尔展示了一部拉康式的《头脑特工队》。皮克斯的这部动画片只演绎了五种情绪(欢乐、悲伤、恐俱、厌恶和愤怒),而索莱尔考察了各种情感。她对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热情修正了精神分析行为和情感范围内的已有观点。她对情感的重新定位将对当代无意识理论产生持久的影响。
帕持里夏·盖洛维奇 (Patricia Gherovici)
作家、精神分析家
正如人们对克莱特·索莱尔的地位和经验所期望的那样,《拉康派论情感》为训练有素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阅读,且各流派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也可以从中获益,他们会发现拉康对情感的思考将为他们的临床工作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
朱迪斯·汉密尔顿 (Judith Hamilton)
医学博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多伦多精神分析学会成员

重读这部2011年出版的作品后,我再一次想要为它做些什么。然而时光易逝,精神分析圈子中争论的焦点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几乎听不到那些“大人物们”教训拉康,说他对人类的情感漠不关心;相反,作为精神分析家和临床工作者的拉康已经举世闻名,然而,只是在“大人物们”自己的圈子里,诽谤的声音逐渐平息。拉康曾经说过,21世纪将是拉康派的。但要保证精神分析的胜利,我们仍需更多努力,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回到了另一个极端:机械决定论的支持者们,与那些坚持让言在主体承担自身冲动之责任的人们之间的古老斗争再一次出现了。我们之所以回到这一古老的争论,很明显是因为生物科学的进步,生物科学由此挽救了所谓的神经科学中那些公设的霸权性。这股风气对精神分析极为不利。
我在《拉康派论情感》中提到的那些情感,拉康曾经激情洋溢地评论过,但这些情感并不是都处在同一个层面。其中,焦虑具有一个独特而主导性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也不仅是因为弗洛伊德在1926 年将之视为症状的创伤之因,同时也是分析终点的岩床;还因为拉康曾经为此做了一年的讨论班,正是在这个讨论班中,他构建了客体a这一概念,这也是他(理论上)的主要创造,这一概念被定义为在想象、符号、实在的三界中的“缺失之物”。客体a是一个驱动者,它不固定,但它保持静谧,如同人类这架机器运作的噪音,正如拉康所说,客体a带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整个现实”。如今,它更是前所未有地成了“社会的穹顶”。
尽管如此,拉康对这些情感的阐述中,最微妙、最原创的看法却体现在其他地方:只有拉康重视了这些情感,并认识到了其启发性的功能。首先,就是分析后的“不可预知的情感”。我借用了他在“巴黎弗洛伊德学院讲座”(Discours à I'EFP)中的这句表述。我曾说过,那些进入一段分析的人们都希望,最终他们只会有与情景相匹配的情感。但很遗憾,经验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同样,只有拉康考虑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而非将之归因于神经症的复发。同样,我们只有提出一个假设,即情感是语言装置产生的一种“效果”,才能认识到在那些神秘、意外的突发情况中出现的信号,这种信号并不代表着能指链,而是代表着啦啦语 (lalangue)。前者的效果在分析中得到了探索;但后者充斥着数不尽的模糊,永远孕育着新的情感。我所谓的情感的证明,可以补充拉康所谓的能指对无意识的证明。
我已经提到过,在拉康讨论可结束的分析的最后一篇文章《第十一讨论班英文版序言》(Préface à l'édition anglaise du Séminaire XI)(简称《序言》)中,他的另一个原创性观点也很清晰,即其反对弗洛伊德对于不可结束的分析的看法。拉康在文中提到了一种新的情感,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不是对随便某些事物的满足,而是对······(分析)的结束的满足。这一看法在拉康其他文献中是找不到的。这是一种分析本身带来的治疗益处,因为它可以在分析的结束时抵消言在主体,尤其是那些弗洛伊德式的神经症们那种普遍的不满。并非在那篇文章里,拉康第一次提到分析的结束带来的益处,自《言语和语言的功能及领域》(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拉康持续的思索。他曾经一直在探索,直到提出了主体的“变形”。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拉康更进一步,因为这种满足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感,它标志着一种超越了主体性转变的存在的转变。
我们认为:情感这一概念假设一个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另外,言在主体有两个被影响者,因为他有身体,身体被享乐所影响。而享乐又被语言所否决和切碎,于是享乐也影响着身体本身,因为身体不可能不遭遇享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体验”。我模仿拉康在一篇文章里的说法,于是可以说:“(作为)精神分析家,我对情感保持警觉······”因为(情感)就是我最初也是最终要处理的内容。联系着症状的痛苦、焦虑、抑制的情感,就是我们最初呈现给分析家的内容,而分析的最终则是解决性的哀悼、赞同,甚至满足的情感。我所模仿的那篇拉康的文章明显有另一个意思:“(作为)精神分析家,我对信号保持警觉······”,信号并不是能指,但它和能指有共通之处,即都是一个有关联性的元素,但是信号的基础是数字,在语义效果上与能指秩序截然不同。“信号的信号”意味着,一者等同于另一者,彼此可替代,因此其意义并不是语义上的,信号有关于享乐,既存在于永无止境的对无意识形成物的解码过程中,也存在于无法动摇的症状的固着中。随后,被影响的享乐也会反馈到言在主体的情感中,我对这种“结感”(effect)保持警觉,与此同时,对其加倍的“信号”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当然是通过这类信号而运作的,因为分析解码着无意识所编码的内容,但是情感的功能更清晰地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情感就是一种信号,在指示着什么这个一般意义上而言,这种信号与其说是无意识的编码者,不如说是存在相对于其无意识的位置。
因此,我要强调我在本书最后引入的内容,也就是自1976年的这篇有关分析者的,有关分析结束的《序言》以来,精神分析中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总体来说,拉康很清楚,无意识的这一维度是不可缩减的,它永无止境地在替换这些超出了“意义”的信号,《序言》中说“无意识了解自身”,但是根据拉康的说法,他也知道,关注这种信号,也就是从中抽离出来,抽离出它的“无意义性”,从而还给它一种“真相的意义”。(分析的)结束,其实也就是“对真相之爱”的结束,这种爱与所谓的“自由联想”其实是一体的。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仍然纠缠在这种爱中,为了创造出一位分析家,后者不得不把分析做到底。此外,弗洛伊德的全部兴趣都在此,因为半说的真相具有阉割的效果,弗洛伊德只好悲叹道,他拒绝着这种结束。这道“岩床”本质上内在于他对(分析)实践的概念化。
拉康在1967年就用《1967年10月9日给学派分析家的提议》(Proposition sur le psychanalyste de l'Ecole)反对了弗洛伊德的看法,这篇文章提出了分析结束的解决方案就是一种主体性罢免——但并非不带有一种哀悼的意味。然而,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从言说真相的转移空间中能得到什么?得到的只是一堵“岩床”盖在半说之洞上,而正是在那里,幻想的客体a浮现了出来,这就是去实质化的主体所唯一拥有的东西。但是,无意识的运作只针对那些超出意义的信号,这种运作在这方面是实在的,也是另一回事。于是,我们应当从此——从那篇《序言》开始——思考我们每个人相对于无意识的双重位置,或者说相对于双重无意识的位置:一重是主体的能指链中的位置,另一重是实在的位置,后者补充了拉康自“精神分析的行动”这一讨论班的总结报告开始,关于“无主体”的、超越意义的,但与享乐相关的无意识的概念化思考。
然而,我们的思考并非一种朝向实在无意识的“通过”。在拉康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友谊”能阻止转移之爱的风蚀。拉康的方向对于他者(渡者、卡特尔、见证人)而言,只体现在一件事上:真相之幻的终结,当对结束感到满足时,这种满足感本身就独一无二,可以替代对真相之爱。在《序言》这篇文章里,这种满足感使得分析者对“自由联想”(包括梦境)失去了兴趣。这并不是说从此开始,主体进人了”无意义“的无意识中,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重复性趋势虽然削弱了表达真相所带来的价值,但并不能彻底消除后者,于是主体体验到了某种“不可摧毁之物”——或者说超验之物——这便可以平衡无意识上述的两个维度······这就是令人满足之处。
我们或许要看看,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在“通过”机制中加入这一新的视角,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