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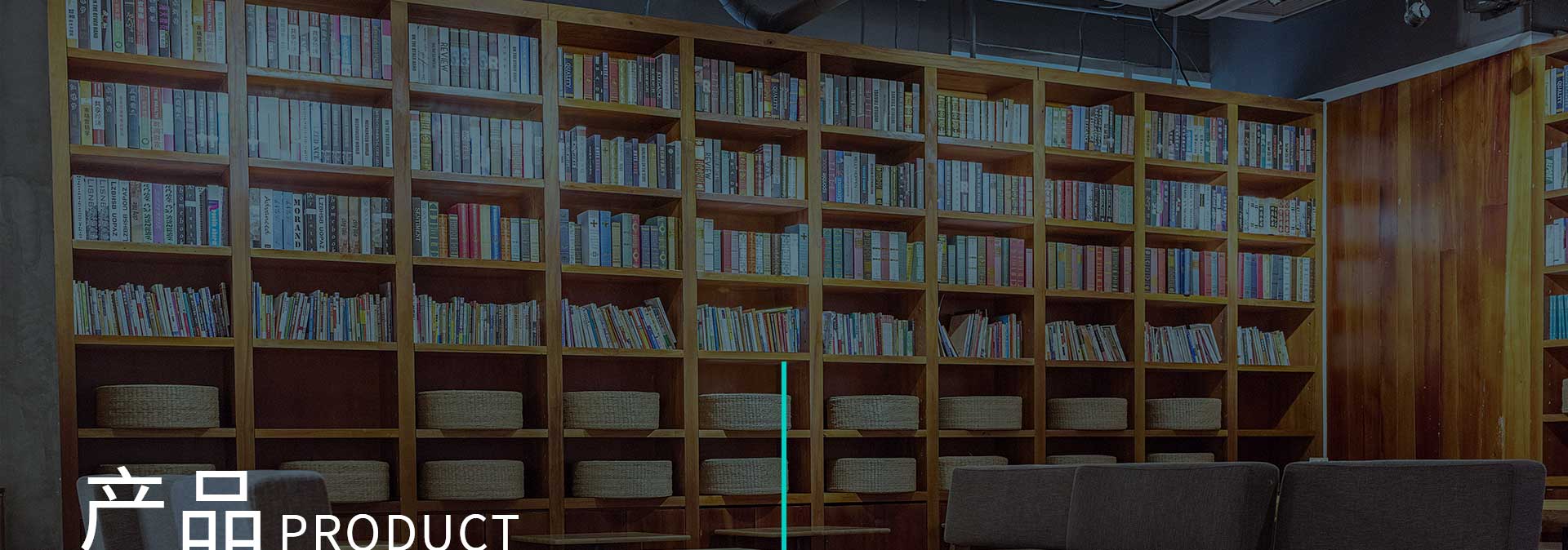

她,即是浪潮

《女子教育》
迄今为止,我所提到的只是那些父母会为其安排好生活的女性。可是还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至少受过时髦教育的女性没有钱。她们但凡还留有一丝敏感,就经常只好单身。
谋生的方式很少,有也非常丢人。或是给某个有钱的老亲戚做个卑微的伴侣,或是和暴虐到无法忍受的陌生人一起生活,后者更糟。因为就连亲戚都无法忍受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哪怕能从这样的人那里继承一点钱。这样一个谋生者必须度过多少痛苦的时光真是无法计数。她的地位处于仆人之上,却被仆人视为间谍。
她和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谈话时,永远都被提示着自己的卑微。如果她不能屈尊逢迎,她就不可能成为受欢迎的人。如果有访客注意到她,而她一时忘了自己的从属地位,她也一定会被人提醒。
她对不友善有着痛苦的意识,她对每一件事都很敏感。很多挖苦的话也许不是对她说的,却被她听到了耳朵里。她孤身一人,被排除在平等和自信之外。埋藏的焦虑损害了她的体质,因为她必须面带愉快,否则就会被解雇。在这种约束状态下,虽然依附于同类的反复无常是事出必要,但这仍然是一种无比痛苦的矫正。如果能回避它,我们会很乐意。
学校里的教师只是一种上等仆人,他们做的工作比卑微的仆人还多。
教小女孩的家庭女教师同样令人厌弃。她们十有八九遇到的都是不讲理的母亲。这样的主母不断找茬,以证明自己并非无知。如果学生没有进步,主母会生气。可是如果教师采取适当的方法让学生取得了进步,主母还是会生气。孩子们对家庭教师不仅不尊重,还经常傲慢无礼。生命就在这当中消逝了,灵魂也随之而去。“当青春和热情的岁月不再时”,她们将无可依靠。或许,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她们能得到一小笔津贴,已经是雇主大发善心了。
剩下几种职业现在正逐渐落入男人之手,而且当然也不是什么体面职业。

《北欧书简》
为了不让水手们继续操劳下去,我立刻让人把行李搬到了中尉的船上。中尉既然会说英语,我就不必和他再交谈什么了。然而玛格丽特尽管尊敬我,看到我把自己交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手上,脸上还是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惧之情。中尉指了指他的小屋,我走近时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我的心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不像玛格丽特那样一直在想抢劫、谋杀或者另外一桩罪恶。用水手们的话来说,那桩罪恶能立刻冒犯所有女人的想象。
一进门,我就更高兴地发现屋子很干净,还有几分乡村的优雅。床上的铺盖是细布做的,虽然粗糙,但是洁白得耀眼。地板上撒了一些杜松子的细枝(我后来发现这是当地的风俗),与窗帘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一种清新宜人之感,缓和了中午的热度。然而,没有什么比殷勤好客更令人高兴的了,这家人所能提供的一切食物很快就摆放在了最洁白的亚麻桌布上。还记得我是刚刚才下的船吗?我尽管不挑剔,在船上的时候却一直感到恶心。而眼下,鱼、牛奶、黄油和奶酪,还有——我很抱歉地补充一句——白兰地,这个国家的祸根,都已经在餐桌上摆开了。饭后,好客的主人带着某种神秘,给我们端来了一些上好的咖啡。我当时还不知道咖啡是违禁物。
这家的丈夫为不停进来表示抱歉,但是他说他很高兴能说英语,因此他不能待在外头。他不必抱歉,我对他的陪伴同样感到高兴。对他妻子我只能报以微笑,她则仔细观察我们衣服的样式。我发现是我的手最先让她发现我是个女人。我在礼貌方面当然自有分寸,而北地的礼貌似乎掺杂了他们气候中的寒冷,以及那种以铁作筋骨的岩石般的坚硬。然而,在这群燧石之地的农民中,有着那么多黄金时代的纯朴,那么多洋溢着同情心的东西,所以尽管我很累,尽管他们一直让我站着,尽管他们一次次地失礼,我的脸上仍有笑容绽放。只有仁爱和天性中真诚的同情能让我做到这点。

《勃朗特迷思》
如果二十岁时的夏洛蒂·勃朗特得知自己有朝一日会家喻户晓,她的画像会被陈列在英国国家肖像馆,甚至有远自日本的朝拜者慕名而至哈沃斯,她兴许会高兴,但绝不会吃惊。夏洛蒂在《埃利斯与阿克顿· 贝尔的生平说明》中将三姐妹刻画为“不张扬的女性”形象,不求闻达。但夏洛蒂早先的志向绝不单纯止于写作,而是“成为隽永”。
夏洛蒂·勃朗特于一八五五年去世,时年三十九岁,那时的她已然声名鹊起。两年后,随着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付梓,她成为传奇。然而她从平平小我走进公众视线的道路却比二十岁时幼稚的她想象中的要曲折不少。从默默无闻直到取得文学盛名的“光辉与荣耀”,她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尽坎坷。一路上,她既谦避又张扬。
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女作家”都“易遭受偏见”的时代,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开来,用听起来男性化的笔名来掩盖自己的性别可谓权宜之计。笔名能让她在自己的小说中自由地将自己的情绪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础,进而革新对女性内心世界富有想象力的刻画。她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描写如此恣肆以至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震惊了许多时人,甚至被指责具有女性不应有的主张、病态的激情以及反基督教义的个人主义。
当她笔名背后的真实身份在文学圈面前被揭开时,夏洛蒂不得不找寻新的保护“面具”以分散公众对她小说中不可接受的元素的注意,转移对她本人道德的抨击。作为一位乡下牧师未出阁的谦逊女儿,她从这一社会人格中找到了保护。她在文学圈子面前违心地坚称,自己不过在外在方面和叛逆的简·爱有着些许相似罢了。与身着男装并拥有众多高调情人的法国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不同,夏洛蒂从不追求放荡不羁的生活。桑在小说中对女性欲望的直白刻画或许影响了夏洛蒂的写作,但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她从未准备牺牲自己的体面。她很清楚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驰声走誉……对于一位女性而言……若非增光,便是抹黑”,而盛名与恶名之间也仅一步之遥。

《激情精神:阿尔玛·马勒的一生》
(英) 凯特·黑斯特 著;庄加逊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谱
他声称自己对她的所谓“必须保持真我”的固有观点感到困惑,在谈及“所有的恐惧和疑虑”之前,他首先应对此有所厘清。她在信里泾渭分明地写着“你的”音乐与“我的”音乐。这是个必须即刻探讨清楚的问题,两人必须在下次会面之前弄明白。“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把我的音乐视作你的?”他问道,在探讨下一个问题之前,需要了解的是:“你如何想象同为作曲家的夫妻的婚姻生活?你知不知道,这样一种特殊的竞争关系,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多么可笑、多么丢脸的关系。假设你忽然创作灵感迸发,亟需提笔时,你又不得不兼顾家庭或者照看我的需要,那究竟该怎么办呢?”马勒并不赞同资产阶级的婚姻观,也就是把妻子视作供人赏玩的对象兼管家的角色。但他坚称:“如果我们在一起想获得幸福,你必须是我的妻子,而不是我的同事。”
问题的症结在于:
如果你为了占有我的音乐,为了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放弃你的音乐:这对于你是否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如果你当真如此以为,那么你不觉得你同时也是在放弃一个更高的存在吗?在我们考虑建立终身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我心里明白,若要你令我快乐,你自己也必须快乐(为了我而快乐)。然而在这部戏里……你我的角色分配必须得当。“作曲家”的角色,“养家糊口”的人属于我;而你是友爱的伴侣,与我心意相通的同志……你必须无条件地把你自己交给我,让你未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完全取决于我的需要,除了我的爱,你别无所求!……如果你成为我的妻子,我会用我的方式来爱你,我愿意因此赌上我的一生以及我全部的幸福。
信末,他要求她于两天后,也就是他回来之前给一个坦率的答复;届时,他会派人来取信。
读到这封信的阿尔玛简直“目瞪口呆”。
我的心脏几乎在一瞬间停止了跳动……放弃我的音乐——放弃迄今为止我生命里全部的、唯一的意义?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我难以抑制地哭了起来——因为我明白我爱他。我悲伤得几欲发狂,披上华服,驱车前往剧院观看《齐格弗里德》的演出,泪流满面!我把这事告诉给了波拉克,他被激怒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这样的事。我觉得好像有一只冰冷的手把我的心从胸膛里掏了出来。
海伦·文德勒

《大海、飞鸟和学者:文德勒论诗人与诗》
如果说发现抒情诗领域是我批评生涯中最果决的事,史蒂文斯的影响——让我看到自己对语言和结构特征的强烈兴趣——是最奇异的事,那么,1967年,我三十四岁时,最痛苦的事来了。我离了婚,一个人拉扯 儿子戴维,只拿最低的子女补助(每月九十美元),一年拼命讲十门课——每学期四门(其中一门是超负荷的夜校课),每个暑期两门。1963年,我关于叶芝的博士论文已经出版,但在那之后,我一直无法连贯写作。一本关于乔治·赫伯特的书搁浅,因为我意识到,要写这本书,必须深入研究文艺复兴诗歌,但我那时根本没有时间。一本关于史蒂文斯的书已经开了头,但我的精力不济了,也没钱请人看孩子或做家务。一个筋疲力竭的夜晚,我努力思考着怎样让生活变得轻松。显然,我不得不继续教书管家带娃。唯一可以让我过得轻松点的办法是放弃写作。“它们绝不能让我——”我暗想着,惊惶,恐惧,愤怒。“它们绝不能让我 这样做。”我以为“它们”指的是命运,或星宿,但我知道,停止写作是一 种自我谋杀。我决定申请富布赖特资助,暂时休息一下。
由于儿子是独子,我觉得他需要家中有人陪伴,于是决定:他在家并且醒着时,我决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习和教书生活——对我来说无法与写作生活分开——是碎片式的,常常疲惫不堪,永远令人焦虑。随着儿子的长大,他入睡后宝贵的夜晚时光严重缩水;不久,像任何青少年一样,他比我睡得还晚。我的研究和写作生活始于凌晨时分,与我的生理节奏相反。我嫉妒我的男同事们,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伴侣似乎为他们做好了一切。玛乔丽·尼科尔森曾撰文说女性学者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妻子,这再真实不过了。
我最初的行业经历来自读研究生时哈佛英语系系主任对我的警告。公开试听周期间,他在我的听课卡上签字时说:“你知道我们这儿并不要你,亨尼西小姐:我们这儿不要任何女人。”我颤抖着离开他的办公室。(十三年后,他道歉了。)一九五六年,有些教授还不允许女生听他们的专题讨论课。几乎所有被哈佛英语系录取的女博士生都走了。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没有人理解女性成功的基本困难:女博士跟随她们非学术圈的丈夫进了城,那里却没有大学或学院;或者去了学院,那里任人唯亲的规则却禁止女性在其丈夫工作的地方就业;或者去到只要男老师和男学生的学院;或者去了不愿雇用已婚生子的女性的大学。要生多少孩子才算“正常”,生完孩子后就不再工作,这种社会压力特别大。人们普遍怀疑女性的智力。当女博士被这些因素击败半途而废时,教过她们的教授们就更加怀疑为这些或许永远不会干这一行的学生投资的价值。来到哈佛研究生院读书的女生深感自己处于次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