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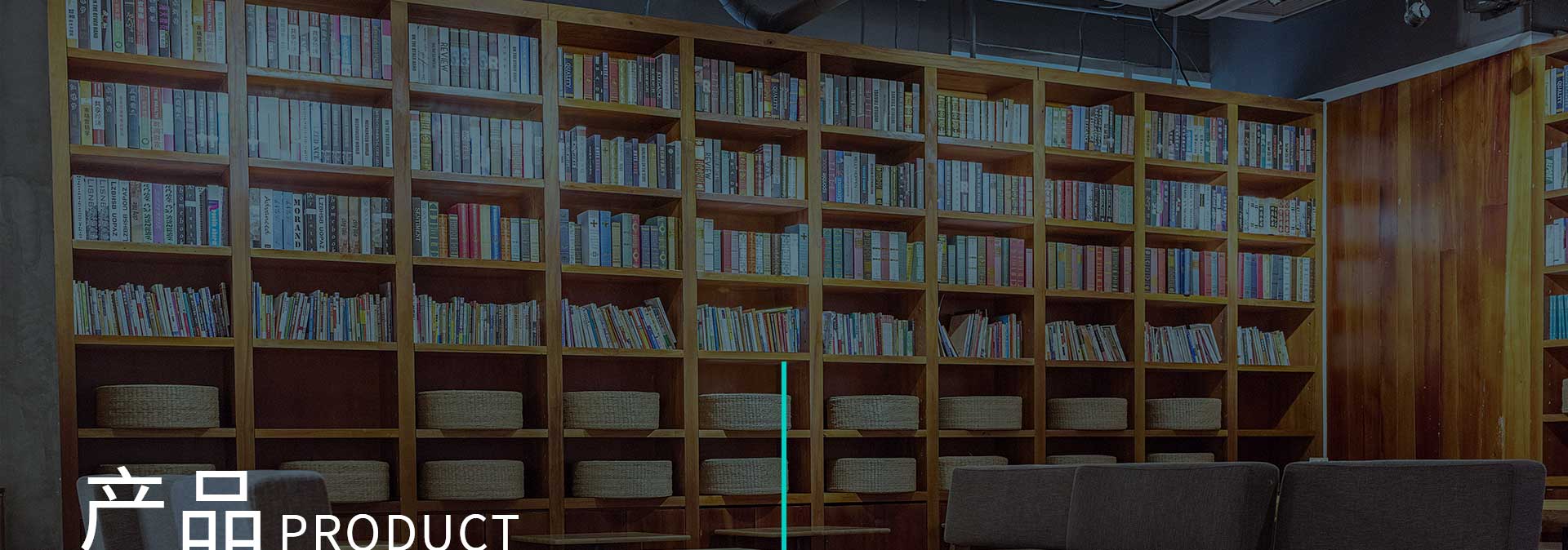

灰娃诗歌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于沪上举办
在研讨会现场,诗人杨键做了精炼陈述:“灰”是20世纪的背景,“娃”是诗人,“灰娃”这个名字理应成为汉语诗歌受难和不死的象征。
作家金宇澄在创作了《繁花》《回望》等著作之后,他的绘画作品也吸引了大众目光。在《不要玫瑰》中,他看到了灰娃诗歌中的画面感,金宇澄直言灰娃的每一首诗,都可以让优秀的插画家去配画。金老师还评论道:“一般年纪大的作者,以及从年轻到年老的作者,会老化,会有一种样式,但是灰娃的独立性给我很强的感受,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感受,她听从一种召唤,我一定要这样做,给人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让人看到另外一种风景。每一首诗,都可以配画。”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则从他的父亲辛丰年当年两次前去见灰娃的往事谈起,他认为灰娃的声音不是孤单的声音,有很多应和的声音,前几天露易丝·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算一个应和,严锋说:“现在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别说诗歌了,连文学都可以不要了,可是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时候颁给了诗人,颁奖词居然还说:充满诗意的声音和朴素的美,使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其实灰娃的诗也有这个特性。”
“有些诗,没有再回看的余地,但是灰娃的不一样,真正的好诗,是可以重复读的。”陈子善教授评论说。
出版人王为松说:“灰娃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这个时代的冷暖,哪怕有细小的温差,她都能敏锐地体会到。灰娃的诗给我的感觉是很大的恐惧感,诗歌构成了生活真相的一部分,如果这个真相是令我们恐惧的,我们要反思。”
活动中场,丁薇老师和家属冷山朗诵了灰娃的诗作。
诗人陈东东从诗歌研究的角度给予了专业解读,他提到灰娃的诗歌发生机制,诗歌观念非常不一样,诗歌出现在她身上,可以说是一种自白,自白的强度,像是从身体里分泌出来的,是一种语言的分泌物出现在纸上。他总结说:“很多批评家在评论诗人的时候,说这个诗人是中国的阿赫玛托娃,说那个诗人是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说灰娃就不需要,她就是中国的灰娃。”
诗人、文艺评论家孙孟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上帝还是很公平的,灰娃同时代的诗人其实是有光环的,灰娃没有得到诗歌的光环,却得到了神性的光芒,我在她的诗歌里获得了人美好、宽容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一个人一直在苦难里透不过气来,这是没有希望的,我在她晚期的诗歌里看到了爱。”
作家小白也出席了本次活动,他说:“今天看到灰娃老师刚才说话,又像小孩,又像看透一切,经历了生活当中的痛苦折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通过在文字当中,在诗歌当中,不知道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也许是摆脱了这种痛苦,也许是给自己建立一道屏障,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诗歌的力量。”
出版人黄昱宁老师说:“诗如果要去解释的话,是徒劳的,但是大声朗读,是有效的,视觉表现,是很重要的。从同行的角度来说,我要赞美这本书,做得很好,光用纸就有好几种,装订形式很复杂,能完全摊开的裸脊是最适合诗歌阅读的。其中冷冰川的插画更让人惊喜,以前看到冷老师的作品都是非常黑的,这一次不一样。”
盛韵博士说:“我是一个翻译,看到文本我就会想象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诗是最抵抗翻译的,跟语言特性结合越紧密,越难以翻译。其实恐惧感这种情感是最容易翻译的,可难以翻译是和语言附着最紧的那一层东西,比如金宇澄的“不响”很难很难,灰娃的“不要玫瑰”没有主语,“我额头青枝绿叶”全是名词,“文豹”衍生出来的文质彬彬的意思,这些都该怎么翻译?”
灰娃新书的设计师周晨也专程从苏州赶过来,周老师说:“灰娃老师之前有好几本诗集出版,基本是黑白灰色调。这次还是灰,尽管大家看到是偏绿色调的,但里面有不同的纸张,还配了一些植物,跟绿色有关系。从灰娃老师诗歌的意境里,青枝绿叶、长青藤、有很多植物的意向。灰本身也是很丰富的,并不是我们看到黑白灰的灰,事实上灰可以有很多倾向性。我觉得这个灰也可以暗合灰娃老师的诗的丰富意境,表达出一种生命力。书的边缘也做了绿,都是想表现自由生长的、生命时间的感觉。”
在研讨会的最后,当代艺术家冷冰川以家人的身份总结点评了灰娃:“没有规循的抑制性的写作,灰娃的诗歌一直有这种动力去写,表面上看似洋溢着欢歌和色彩,其实我认为很多东西是相反的。我甚至觉得她写作的根本体现就是一种无助和愤怒......她的每个字反复都是从生命地底下喷出来的火热岩浆。从上世纪20年代到现在,只有像她这么丰盛的阅历,才能有现在追求的洁净的丰厚的灵性。她在写现实生活的灰娃日记,那么复杂的东西都已经过完了,现在只剩下最简单的。她是一个绝对的在自由渴望中写作的人,可能正是因为种种的绝望,反而表现出她对良善和自由与正义渴望的强烈。我一直在心里有一个形象,她是一个住在近代苦难史上像仙人一样写作的浪漫诗人,这是她人生必须要做的作业。”
